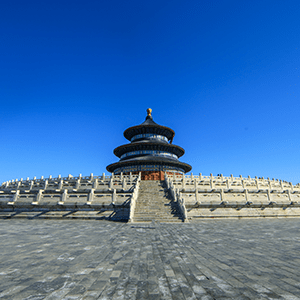历史文脉 | 调控漕运河水量的东闸
北京市昌平区马池口镇东闸村曾经依河傍湾。元朝时期,官府曾在这里立水闸调节水量,以便天下漕运。

东闸村门楼
《元史·河渠一·双塔河》记载:为了养护河道,保证水路运输的安全,避免溃堤成灾,至元三年(1266)四月六日,巡河官上奏朝廷,请求疏浚河道,加固堤岸。元世祖忽必烈遂命北京都元帅阿海率所部施工。阿海不但按要求完成了任务,还按都水监的设计,用工2155个,修建闭水口五处,建河闸两道,按其方位称为东闸、西闸,以控制河道水量,确保水路运输的顺畅。
如今,站在昌平区马池口镇东闸村头四望,昔日水可泛舟的景象已杳如黄鹤。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似乎亦对那段“落景余清辉,轻桡弄溪渚”的历史日渐生疏。虽如此,其“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的美好姿态却仍旧在史册中熠熠生辉。
因河而闸
出生于1940年的薜玉山曾经听村里的老人说过,早先,村子里确实有一条东北-西南流向的河,河上还有一座用于调控河水流量的水闸,而他们村名字的由来,相传还与这座水闸有关。他说:“河闸东边的村子称东闸,河闸西边的村子称西闸。”
流逝的岁月,不仅使得水闸荡然无存,就是传说中那条东北-西南向的河流,也像从来不曾存在过一般销声匿迹了。以至于一旦说到村中的河流,人们只能记起村西那条西北-东南向的河。“这条河往下流,就到了温榆河。”薜玉山说这话时,其他几位老人均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可能是曾经当过村干部的缘故,相较于其他几位老人,和薜玉山同年出生的王书敏则更为健谈。他说,村西河就是从北沙河的源头北京市昌平区阳坊镇四家庄流下来的河水,虽说与村西北方向的四家庄相距也有十余里地,但由于那里的大泉眼出水量惊人,再加上沿途大大小小河流的汇入,到东闸村时,河水量自然十分惊人。“传说以前村子里到处是水。最少时也能达到七八个流量。”王书敏笑呵呵地说。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奔腾的西河水方如野马收蹄般水量渐减。
既然几位老人一再将温榆河和北沙河挂在嘴边儿,看来这条河对他们的生活影响不可谓不深远。北沙河又称大沙河,元代称双塔河,顾炎武在《昌平山水记》中始称其为北沙河。北沙河不仅是温榆河四大支流之一,更是温榆河的正源。这条发源于昌平区阳坊镇四家庄的河流,“径双塔村东流……入通州界,注于白河”,全部流域面积为546平方千米,干流长约20千米,河宽60~100米。追根溯源,北沙河之所以水量浩大,除了得益于支流众多外,更重要的,则是与其上源为关沟水有关。而关沟水与北沙河的关系,《温榆河》曰:关沟水在崇山峻岭中蜿蜒南下,入昌平境,一路汇聚兴隆口沟、狻猊沟、柏峪沟、白羊城沟、高崖口沟等山间溪水,经双塔村(今属海淀区)以西合流后,称北沙河。
如今,水量锐减的北沙河从西北蜿蜒而来,又从村西悄然走远。“河床宽二三十米,水宽十多米,水深不到一米。”亲临现场拍摄的刘勇智说,“水里还有芦苇。”虽然昔日汤汤河水已不得见,但其辉煌的过往却依然在历史典籍中顾盼生辉。
聊天过程中,几位老人时不时地就会提到双塔河、提到北沙河,同时,也提到温榆河。虽然他们并不十分清楚这些河的前尘往事,但他们却很清楚,曾经,他们村也是响当当的丰水区。那是村庄的记忆,也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骄傲。
缘闸立村
地处北沙河东岸的东闸村,现如今已没有了水光潋滟的旖旎风光。东闸村以前遍地是水的说法,也只是一代一代的村里人从老辈人那里听来的。不过,这些年来几乎每年都会来一次的文物部门,却又让村里人觉得,他们村应该确有“东西”,不然,这些考古人员干嘛大老远地总往这儿跑呢?被问及“东西”是否就是指“东闸”?他们露出波澜不惊的神色道:“可是,这有什么可看的呢?”话虽显得颇不以为然,但为了证实村里的确挖出过东西,出生于1935年的刘瑞河还是补充了一句:“村里以前挖沙时,倒是挖出来过一些麻石(大理石)。”
东闸村面积不大,也就一平方公里左右。解放前,东闸村还是一个与地处村北的北庄户合二为一的村庄,那时,村里人口尚不足三百人;村里人的口粮主要以玉米、小麦为主。解放后,两村分离。刘瑞河清楚地记得:“那时,我们村还种过五六年水稻。现在村里全是林地,没有人再种庄稼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村里还兴起过一段“挖沙热”。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埋在地下的“东西”有了重见天日的机会。

东闸村河流故道
也许正应了那句“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老话,虽然如今的东闸已引不起本村人多少兴趣,但历史上,有关东闸的话题却着实不少。单从名字论,《昌平史迹要览》即有:东闸,水利工程之截流设施,现已演变为村落,位于昌平区马池口镇;《温榆河》亦有:清代时,在昌平北沙河畔还有村曰‘西闸’‘东闸’(位于今马池口镇),此即当年白浮堰截流工程的遗迹等说法。
而与其相关的白浮堰截流工程,时下却随着对三大文化带的发展与保护,变得广为人知。建于元世祖忽必烈时期的白浮堰截流工程,系科学家郭守敬为解决大都(今北京)城用水而兴修的一项水利工程。工程“起白浮村到青龙桥,延袤五十余里”“以障双塔、神山诸水使东南流入潞河,以便天下漕运”。
漕运顺畅的前提之一便是水量充足。因此,选址建河闸便被提上日程。竣工后的河闸就像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呼唤着各色人等纷至沓来。对于东闸的成村史,《昌平镇村探源》一书述称:“明朝初期,供应居庸关守军的仓场虽然前移到了居庸关内的金柜山下,双塔河仍然发挥着运贮军粮的重要作用。守军们在河闸附近娶妻生子,繁衍生息,逐渐形成村落,他们就以河闸作为标志物,因村子坐落在东闸立闸之处,遂称为东闸村。”
虽然,今天大多数东闸村人已说不清村名的由来,人们也并不关心自己是不是守闸人的后代,但,作为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东闸终归是他们剪不断的情感依附。因此,若有人扯起话头,人们倒也乐意聊聊村庄旧事。
这不,接着挖沙的话题,72岁的包文永就十分肯定地说:“挖出来的麻石有这张桌子这么长,这么宽。”他的两条胳膊在胸前比划出一个五六十公分长的距离,麻石的宽度也便由此清晰起来。再目测一下他面前的桌子,则大约有两米多长。包文永之所以对麻石的大小了解地如此清楚,是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挖出这些条石时,他就在现场。他说,由于这些条石不在同一个方位,在场的人当时就猜测,这些条石的中间应该是一条河道,而这些条石,则很可能是用来墁河两侧堤坝的,而传说中的闸口也许就在这附近。听了他的话,几位老人有表示赞同的,有嗤之以鼻的。持反对意见的人问:“挖出来几块儿条石,就能证明这里有河闸?”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村里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一旦起了争执,竟然也会像小孩子吵嘴一般各不相让。
好在,事实胜于雄辩。对东闸的记录古已有之。清代麻兆庆编撰的《昌平外志校理》就载有:州南有东闸、西闸二村,东闸在双塔河北,西闸在双塔河南,西去双塔村,不过一二里。与此契合的是,2011年出版的《镇村探源》明确道:东闸村西距海淀区上庄镇双塔村1公里……
由村及庙
东闸村的关帝庙,即便山门门楣上赫然写着“关帝庙”仨字,村里人也依然对此命名不大认同。问及原由,老人们七嘴八舌地争相发言。他们言语肯定地说,上世纪五十年代,这座庙还有三尊泥塑,至于这些泥塑是谁,虽然由于当时年龄小,他们已记不太清,但可以肯定的是,泥塑当中并没有关公像。“庙西还有一小庙,那庙我们叫关帝庙。”王书敏笑言,“为什么?因为小庙的墙壁上画着关公像。”

东闸村关帝庙
东闸村的关帝庙坐东朝西,《昌平寺庙》称,此庙建于明代,山门一间,大殿三间,大殿两边有耳房三间,南北配殿各三间。村里78岁的薜玉山七八岁时便在这里上学,因此对这里的一切记忆深刻。他说,据说村里的这座关帝庙是西沙屯大庙的一个分支……
关帝庙是座四合院。院内有正殿三间,正殿门前,北侧有一棵柏树,南侧有一棵百余年历史的老槐树。由于年久日深,两棵老树树皮尽脱。正殿南北两侧各有耳房三间,耳房与南北院墙连在一起。北侧耳房紧靠院墙处有门可出入寺院。从这里出寺院即是一大片与寺院同等大小的空地,推测原本应为庙产;空地南侧、离寺院南耳房不远处,有一眼用于浇地的古井。老人们记得,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南耳房曾被用作保公所。除了正殿,院内还有南、北配殿各三间。北配殿距院墙约1米,南配殿距院墙约1.5米。南配殿正中一间曾供奉着一尊一米高、七八公分宽的铜菩萨,两侧间扔着一些杂物。北配殿在解放后被当作教室使用,东侧一间供老师住,西侧两间作教室用。若从山门进入,迎面便是一道影壁墙,转过影壁,一间叫作维土店的房子与正殿东西相对;山门南、北两侧,紧靠西院墙处又各有三间房,其中北侧三间住过和尚。薜玉山说,就是在这间房里,他还看到过佛经。
“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满。”倏忽间,马池口镇东闸村已在岁月的长河中跋涉了几百年,如今的它虽少了些水的滋养,但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潮中,昔日“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的景色或许有朝一日会重现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