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一本书,看遍大青山草木
“您很优秀,因为您对植物感兴趣。植物增添了山川的色彩,也成就了大地上的文明。大青山是国家4A级景区,考虑到他人也需要这里的植物,请不要在这里采野菜、挖药材、折草木。至于野果,可以如博物学家梭罗所言,在野地里适当品尝。前提是,您分辨得一清二楚。”《青山草木》一书首页这段话,隐含着作者复兴博物学的目的。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华杰最近出版了一部很有趣的书《青山草木》,专门介绍吉林大青山的野生植物,用精美的图文展现了大青山春花、夏叶、秋实、冬雪的四季景观以及当地常见的花草树木。
一位哲学教授为一个旅游区的野生植物“作传”,这件事同样有趣,也与他近年来致力于复兴博物学的工作有关。围绕这本书和博物学的话题,记者采访了刘华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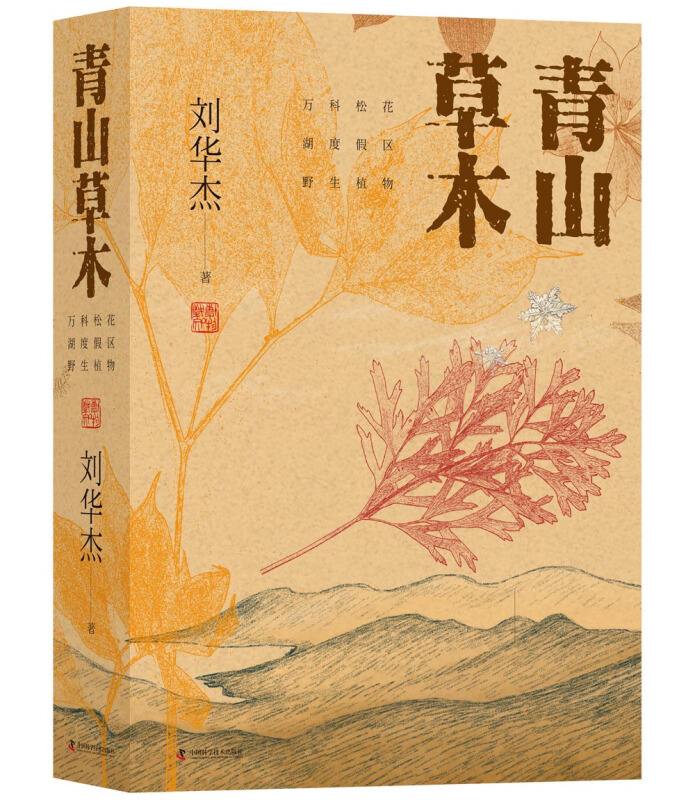
本报记者:博物学这个概念对一般人来说还挺陌生,也是这本书让我们感兴趣的原因之一。什么是博物学?您致力于复兴博物学,向大众普及博物学知识,目的是什么?
刘华杰:“博物”是一个古老的认知传统、生活方式。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博物学文化,中国古代文明不是只靠现在讲的狭义“国学”而发展过来的,除此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物质基础、形而下的方面,博物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就大尺度的人类社会发展而论,靠的也不是只有极短历史的近现代科技、高科技,而是平稳发展的博物学。在英文中“博物”一词是natural history,其中history不是“历史”的意思,而是“探究”的意思。什么是博物学?粗略地看,它是对大自然的探究,但又不同于当下职业化的科学家的探究。博物学主要在乎普通人通过日常的观察、感受来记录大自然的现象,描写大自然中的动物、植物、岩石、矿物、生态系统等。换一种说法,博物是普通人对自然世界的一种“访问”,“访问”的方式和内容非常丰富。
复兴博物学,包含两层:一是二阶学术层面,要研究博物学的历史、人物、博物认知、博物文化、博物艺术等;二是一阶实践层面,指实际参与对大自然的探究,这种探究可以是很随意的,也可以是相对讲究的。我不愿意用“普及”两字,因为它蕴涵了上下级的关系。博物,重在实际操作,重在参与。博物学不同于自然教育,后者热衷于教育别人,而前者重在教育自己、自得其乐。
本报记者:作为一位哲学和科学史的学者,做这样一本书肯定别有深意吧?特别是在环保和生态保护成为当下热点的大背景下,您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刘华杰:一般的哲学工作者不会对植物感兴趣。另一方面,如果我是一名植物学家,恐怕也不会写《青山草木》。现在的植物学家对这类工作兴趣不大。
我没有在课堂上学过植物学课程,只是个人喜欢植物,经常到野外看植物,也自学了一点点植物学。就大的方面看,我一方面吆喝博物学文化,倡导研究博物学史;另一方面想做一个实验,拿我自己做实验,看看像我这样没有专门学过植物学的人,能否认出、理解我所见的植物。实验分三个阶段:近、中、远。我都试过了,结果还可以,结论是:植物就在我们身边,它们是人类的伙伴,普通人可以辨识植物、欣赏植物,并通过观察植物而了解所在地的生态及其变迁。关于“近”,我写了《燕园草木补》,关注的只是我们北京大学校园内的植物,与此接近的还有《崇礼野花》《延庆野花》。关于“远”,我写过《檀岛花事:夏威夷植物日记》,关注的是异国他乡美国夏威夷群岛的植物。关于“中”,我写了《青山草木》,关注的是吉林省吉林市万科松花湖滑雪场的植物。这些书现在看可能都不重要,但我希望50年后、100年后,它们会成为一份可参考的史料。
重拾古老的博物学,确实有哲学层面的考虑。第一是我对现代社会发展的现状极为不满,即对“现代性”持强烈的批评态度;第二是在科学哲学上,受波兰尼的《个人知识》一书和“个人致知”观点的影响;第三是受胡塞尔和梅洛—庞蒂现象学的影响,具体讲涉及“生活世界”概念及“具身”问题;第四是想重写科学史或者人类文明史,尝试提出“博物编史纲领”,现有的科技史和文明史存在严重的偏见,宣传暴力、操纵力,鼓励人们恶斗而不是共生。我们怎么重新书写自然科学的历史?在工业文明遭遇大量问题的当下,天人系统如何可持续生存,如何重塑人类质朴心灵?这些都是我想探讨的问题。
本报记者:作为一个普通读者,会以“好看”来评价本书。本报对此书感兴趣的另外一个原因也在于书中的很多植物与辽东山区的植物很相似,所以感到亲切。“好看”这样的简单评价您会满意吗?
刘华杰:“好看”,就如“有趣”一样,是个很高的评价了,谢谢!博物学的定位始终不离审美和生活,即在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博物还有更基本的一面:好玩,让人快乐。好玩极为重要,它使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有趣,生活质量得以提高。孩子爱玩,成人也一样,只是通常不敢言“玩”。普通人通过观鸟、赏花、登山、生态旅行等,探究大自然的同时,也会获得一种存在感,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博物自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了解大自然和我们自己,让我们自由、自在。哲学家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他发现了“我思”的基础地位,类似的,我们也可以说:“我博物,故我在。”
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中,博物学均十分发达,中国人吃饱饭过上小康生活,博物学也一定会发达起来,我们做的工作是推动。现在正规教育无视博物学,这件事只能在社会上推动。
吉林的植物与辽宁的许多物种一致,我希望通过此书,让人们回忆起与植物的友好交往,重新关注身边的草木。爱家乡,可从身边的草木开始。关注草木,我们的心情、生活品质也会发生变化。我希望这类书多起来,东北每个国家公园、每个保护区、每个景区,都应当有这类手册,现在基本没有。除了植物,也应当关注鸟、昆虫、岩石、蘑菇、哺乳动物、两栖动物和爬行类动物。
本报记者:作为热爱家乡和关注自然的普通人,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特别是对我们这些被城市困住、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大自然、了解植物的人,我们还能“博物”吗?
刘华杰:博物的内容太多了,在城市里,也可以看星星、观云,看动物,最简单的还可以看昆虫,昆虫有100多万种,到处都是,想回避都难。植物也特别容易见到,哪个小区都有植物,家里的一日三餐,也都有植物。走进大自然,不一定非得到遥远的地方,在自己的小区,甚至校园、街道就可以做到。
了解这些事物,对我们的祖先来说是必需的。哪种野菜能吃,哪种有毒,什么动物比较凶猛,怎么判断天气,表征着一个人的见识和生存能力。人说到底是个自然物,不是机械,不是房子,更不是“比特”(信息单位)。自然之物最终是要跟大自然达成和谐,从个体看是这样,从群体上看也是这样。如果个人博物水平很差,即使书读得很好,人格与能力还是有欠缺的,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可能会藐视大自然,以为自己的存活不必靠大自然,我有钱、有房子、有车就能活,没想过车跑在什么地方,钱是从哪儿来的,房子是建在什么地方。这样的文明,是飘在空中的文明,没有根。(记者 高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