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史话丨阮元在瓜洲造“红船”设义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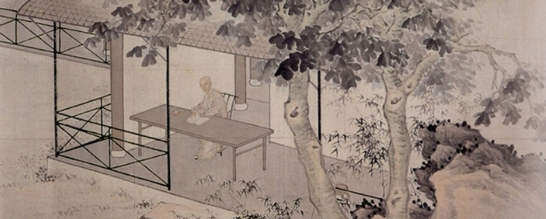
瓜洲,千年古镇,“诗词古渡”。运河与长江情韵胶着的瓜洲,至今仍回旋着一个个美丽的文采华章。且不说白居易“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的愁怨,也不说陆游“楼船夜雪瓜洲渡”的慷慨,仅仅是清代,就有不少人文故事在瓜洲生发。比如,九省疆臣一代通儒阮元,就在瓜洲留下了“红船”义渡,题《曲江亭图》的故事,在瓜洲对岸的焦山留下了建“焦山书藏”的佳话。尤其值得一说的是阮元在瓜洲造“红船”设义渡,为官父母的仁者之行,留作传统,堪为表率。
义举造“红船”,救难如代如来劳
“阮氏义产章程”碑刻中记载:“(往)礼祀洲造红船一只,在仪征、瓜洲一带往来载渡。办事人等,遇有风波便即救生。如救得溺人者,优加奖赏。”
阮元义造“红船”的义举,大约发生在嘉庆十年(1805)左右。所谓“红船”,就是将船身漆成红色,俗称“红船”,专门用于水上救生和打捞。阮元舅父林书门在《邗江三百吟》《大小义举》“救生船篷索”中有云:“渡扬子江最险,两淮另设一种大红船,用两道大篷索,遇有遭险之船,乘风破浪,飞赶护之。名曰救生船。近年,阮伯元中丞亦仿此而行,留于渡口,嘱族叔逵阳公(阮元族叔阮鸿,字逵阳)查察其事。”其诗咏有赞:“江舟欲覆低忽高,之生之死江心号。红莲一朵双樯下,救难如代如来劳。”
诗中的“红莲”喻比红船,“双樯”是指“红船”有双帆,且有系船帆的两根绳子,也就是“两道大篷索”。意思是说,来来往往的江船因不慎或猛浪倾覆,船上人在江心叫喊呼救,阮元造的大红船“乘风破浪,飞赶护之”,代替如来佛祖救众生于危难之际。而义造“红船”的史实,又在2008年阮元家庙修缮中亦有意外发现,藏于东宅第二进天井西山墙上一二百年的“阮氏义产章程”碑刻重见天日,其中有明确记载:“一设立义渡船也:由扬州至僧道桥,路(隔)湖津,宗祠造设大渡船一只,往来载人;(往)礼祀洲造红船一只,在仪征、瓜洲一带往来载渡。办事人等,遇有风波便即救生。如救得溺人者,优加奖赏。各船小修、大修、拆造,届期由塾中办理。官差优免。”从中可见,这位封疆大吏造义船,行义举的仁慈之心。
其实,阮元自己也曾诗赞“红船”。阮元在1819年冬两广总督任上,作《宗舫》诗,并在诗前序曰:“予旧造红船,取宗悫(南朝宋名将宗悫)长风之义,名曰《宗舫》,为金山上下济渡、救生诸用,三面使风,最为稳速。十数年来,创使远行,竟往来湖北、江西诸地,而江西、芜湖等处亦仿造之,为救生之用,所救皆多。近年宗舫之外,又增三舟,予名其一曰《沧江虹》,一曰《木兰身》,梅叔(阮亨,字仲嘉,号梅叔,阮元从弟。)名其一曰《曲江舫》。己卯冬,予由扬州乘此,七日即至滕王阁下,曾奏言此行之速,而上下江长官趋公,亦间有乘此始能速达者。换舟赴岭,留题二诗。”
一诗:金山飞棹本名红,我遣来回楚越中。帆脚远行须把定,莫教孟浪愿东风。
一诗:满江晴雪几舟红,颇似唐人旧画中。扬子江头万里浪,滕王阁下一帆风。
诗中“扬子江头万里浪,滕王阁下一帆风”,在联话之祖梁章钜《楹联三话·红船门联》中记载道:“吾师尝为余述:在江右时,偶以事遣家丁回扬州。恰值风水顺利,朝发南昌,暮抵瓜洲。若非红船,断不能如此快速也。因制一楹,悬于舟中云:‘扬子江头万里浪,滕王阁下一帆风’。”“上联彰显大江东流之势,波涛汹涌,一泻千里;下联含有潇洒倜傥之态,豪气冲天,快意无限。”足见阮元境界高远,神定气闲之风神。
《宗舫》红船为什么如此之快,其中应该有阮元发明创造的奥秘。阮元在工艺技巧方面卓有才能,24岁就著有《考工记车制图解》。嘉庆、道光年间的许小欧在《三异笔谈》中,记有阮元制作的藏虫柜能自动启闭,有开物成务之功;阮元抚赣时,汲取巡浙时打造剿灭海盗战船的经验,设计制造了一种又快又稳的新型船只,名曰“红船”,嘉庆十八九年间,始创于滕王阁下,大江南北均仿造之,利济行人,快如奔马,朝发南昌,暮抵瓜洲。
阮元还有《用余家瓜洲红船为式在南昌造船以为救生诸事之用瓜洲船乘风归去三日至瓜洲矣》诗云:
南人使船如使马,大浪长风任挥洒。(南人,元朝时,称南宋境内的汉族人)红船送我过金山,如马之言殊不假。我嫌豫章无快船,造船令似金山者。鄱湖波浪万船停,唯有红船舵能把。洪都三日到江都,如此飞帆马不如。
诗中豫章、洪都都是旧时南昌的别称。阮元用“鄱阳湖上万船停,惟有红船舵能把”,把又快又稳的“余家瓜洲红船”赞美了一番,对于经常辗转跋涉的阮元来说,快船与快马缺一不可,造出“如此飞帆马不如”的红船,才能在仕学之途上施展“大浪长风任挥洒”的壮怀大志。
建“焦山书藏”,情有独钟《瘗鹤铭》
阮元已经在杭州的灵隐寺建了藏书楼,名曰:“灵隐书藏”,再在瓜洲对岸毗邻家乡的镇江焦山建书藏,他当然也很乐意。于是,依照“灵隐书藏”将焦山的藏书楼就称之为“焦山书藏”。
中国历来藏书之所,或曰观,或称阁,至阮元则据周礼宰礼所治,史记老子所守,开元释氏曰藏,而创书藏之名。阮元于嘉庆十四年(1809),首创杭州灵隐寺书藏。嘉庆十八年复置镇江焦山书藏。其焦山书藏所作所为,尤为志林之雅事。据王章涛《阮元年谱》记载:阮元漕运总督间,嘉庆十八年,正月。一日转漕于扬子江口,阮元“会焦山诗僧借庵、翠屏洲诗人王豫来瓜洲舟次,论诗之暇,及藏书事,遂议于焦山亦立书藏,以《瘗鹤铭》:‘相此胎禽,浮丘着经,余欲无言,尔也何明,雷明门去鼓,……’等七十四字编号,属借庵簿录管钥之。复刻铜章,书楼匾,订条例,一如灵隐。观察丁公百川(淮)为治此事而葳之。此藏立,则凡愿以其所著、所刊、所藏之书藏此藏者,皆裒之,且即以元昔所捐置焦山之宋元镇江二志为‘相’字第一、二号,以志缘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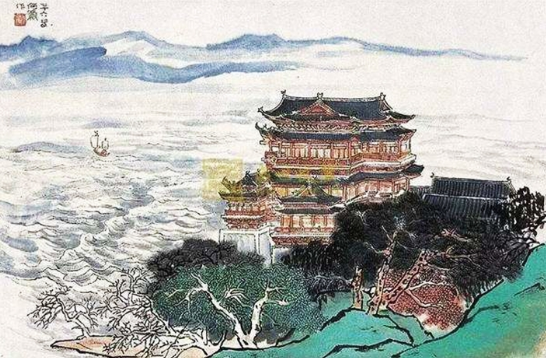
这段文字不多,但其中藏有不为人知的故事:
一是阮元为什么要建立“焦山书藏”。转漕于瓜洲期间,阮元与焦山的僧人借庵以及诗人王柳村(瓜洲诗人,字豫)聊天时,想在焦山上建立藏书楼。这位借庵虽然是僧人,但也喜欢吟诗作赋,因此对藏书之事很是上心。在此之前阮元已经在杭州的灵隐寺建了藏书楼,名曰:“灵隐书藏”,再在瓜洲对岸毗邻家乡的镇江焦山建书藏,他当然也很乐意。于是,依照“灵隐书藏”将焦山的藏书楼就称之为“焦山书藏”。阮元是个有着文化热情的官吏,他说干就干,在第二年就派人在焦山海西庵建起了书楼。而这个海西庵就在华严阁的旁边。藏书楼是建起来了,书从哪里来?于是,阮元从自己的藏书中选出206种,即1400多册,首先捐给了焦山书藏。他的引领示范果真起了作用。此后多年,一直有藏书家给焦山书藏捐书,比如,八千卷楼主人丁丙(清末著名藏书家)就是一位。大约是光绪十七年,梁鼎芬(晚清学者,藏书家)到杭州拜访了丁丙。他跟丁丙讲,在此之前,自己去了焦山书藏,看到了那里的藏书情况很好,他决定自己要捐出一批书,也希望丁丙能够捐书。梁鼎芬是这样说的:“岁游焦山,见书藏未毁,瑶函秘籍,如在桃花原不遭秦火。山僧尚守成规,簿录管钥,虽历七八十年,流传弗替,可谓难矣”。丁丙在梁鼎芬的劝说下,于是从自己的藏书中拿出一部分,他又劝说自己的朋友拿出来一部分,总计451部,即有1000多册,一同捐给了焦山书藏。终使“焦山书藏”名符其实,书墨飘香而名闻四海。
二是阮元为什么以“瘗鹤铭”命名“焦山书藏”。《瘗鹤铭》,刻于南朝·梁(传)天监十三年(514年),有“山中宰相”之称的陶弘景楷书摩崖。存90余字。原刻在镇江焦山西麓石壁上,中唐以后始有著录,后遭雷击崩落长江中,南宋淳熙间挽出一石二十余字,康熙五十二年又挽出五石七十余字。乾隆二十二年嵌于焦山定慧寺壁间,共九十余字。未出水时之拓本称“水拓本”,字数不多;出水后初拓本(五石本)即上皇山樵书。《瘗鹤铭》发现以后,得到历代书家的高度评价。如黄庭坚认其为“大字之祖”,作诗说:“大字无过《瘗鹤铭》。”《东洲草堂金石跋》云:“自来书律,意合篆分,派兼南北,未有如贞白《瘗鹤铭》者。”其书法意态雍容,格调高雅,堪称逸品,是艺术性极高,影响极大的著名碑刻。《瘗鹤铭》石刻崩坏落水后,原文内容至今无法考证,目前流传较广的版本是《金山唐人抄本》。阮元著有《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是清中期的碑学倡导者,对《瘗鹤铭》更是情有独钟,在镇江焦山西麓石壁上有原刻,又于乾隆二十二年将所挽残字共九十余字嵌于焦山定慧寺壁间,因此阮元用《瘗鹤铭》命名焦山书藏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三是阮元为什么在舟中议事。因为阮元官高位爵,拜访和求见官吏及文友甚多,“一品清廉”是自己从政治政的座右铭,因此,宦迹之处谨言慎行,不给同僚属下有请客送礼的机会,于是阮元与借庵和王豫三人便在舟中一边喝茶,一边赋诗,一边又商议起焦山书藏之事。这也说明阮元廉洁自律始终如一,初心不改。
题《曲江亭图》,翠屏洲长焦山北
“扬州城东南三十里,深港之南,焦山以北,有康熙间新涨佛感洲,或名翠屏洲,诗人王柳村(豫)居之。”阮元曾多次游览此地,“京江画派”开派画家张鉴据此绘作《曲江亭图卷》,阮元题诗以志旧游。
翠屏洲是康熙年间由长江流沙淤积而成的一处沙洲,在《嘉庆瓜洲志》中有明确记载。其与镇江的金、焦二山隔江相望,东接城洲,西连瓜洲,北临六圩乡。近百年来,因北岸坍塌,翠屏洲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但从《嘉庆瓜洲志》中还能看到当年翠屏洲美丽的身影,至今还能听到翠屏洲传出的佳话。
阮元《题曲江亭图》诗中云:扬州城东南三十里,深港之南,焦山以北,有康熙间新涨佛感洲,或名翠屏洲,诗人王柳村(豫)居之。丁卯秋余与贵仲符(徵)吏部、梅叔(亨)弟,屡过其地,梅叔买其溪上数亩地,竹木阴翳,乃构屋三楹,亭一笠于其中,柳村又从江上郭景纯(两晋时代最著名的方术士)墓载一佳石来置屋中,予名之曰:“尔雅山房”;又名其亭曰:“曲江亭”,以此地乃汉广陵曲江,枚乘(江苏淮阴人,西汉著名辞赋家)观涛处也。戊辰秋,柳村来游西湖,出《曲江亭图》索题一首,以志旧游。
王豫(1768-1826)活动于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字应和,号柳村,又号翠洲农、小辋川人。镇江人,后移籍江都。丹徒附监生,工于诗,诗风清淡,集名《种竹轩诗钞》。先后辑印《群雅集》、《群雅二集》。还于嘉庆十年乙丑秋,阮元从弟阮梅叔与王豫有接触,议辑《江苏诗征》,阮元知其事,赞同此举,赞助编辑,并于六月二十日,阮元寄书王豫,商榷《淮海英灵续集》、《江苏诗征》、《皇清碑版录》诸书事,并馈赠端砚二方、古墨二盒、江郞山茶二瓶。
阮亨(1783--1859),字仲嘉,号梅叔,清代文学家。阮元从弟。所撰骈体文、古近体诗、词录、随笔、杂记等11种36卷,汇为《春草堂丛书》刊行,还有《珠湖草堂诗钞》、《琴言集》、《珠湖草堂笔记》等。
据王章涛《阮元年谱》:“八月下旬,王豫游杭州,向阮元出示《曲江亭图》,阮元题诗以志旧游。”据此,由清代“京江画派”开派人物张鉴所作《曲江亭图卷》,交由阮元题图当在浙江巡抚任上,为嘉庆十三年(1808)。阮元通过题诗,表现出对家乡扬州的炽热情怀,同时也为扬州曲江留下了宝贵的历史史料。
其实,早在秦汉时期,长江上的广陵涛便已是一大名胜奇观,东汉王充《论衡·书虚篇》中提到:“广陵曲江有涛,文人赋之。”南朝乐府民歌《长干曲》:“逆浪故相邀,菱舟不怕摇。妾家扬子住,便弄广陵潮。”形象地描述了广陵潮波澜壮阔以及当时人们弄潮的景象。
同样在清代,阮元《题曲江亭图》全诗24句,把长江的东流之势,波涛的汹涌之态,瓜洲的沧桑之变,辋川的文人之萃,尽收诗中,品诗赏景,如梦一般徜徉于清溪夹竹,高柳桃花之中。不妨我们对这首诗作一些简要的解读:
“长江千里来巴蜀,流到广陵曲复曲。古时沧海今桑田,翠屏洲长焦山北。”阮元认为,长江发源于巴蜀,流经千里颇有“曲复曲”的感慨,古代的沧海变成了今日的桑田,曲江的翠屏洲在不断的涨起;
“江北横生十里沙,广陵涛变千人家。九折清溪夹修竹,万珠高枊藏桃花。”虽然古代的广陵涛声不见了,十里沙堤已经变成了安居乐业的千户人家;其中王豫和阮亨陶然于环境优美、生态之好,与水毗邻的房屋掩藏在修竹、枊树、桃花之中令人羡慕;
“辋川本合诗人住,况是惠连读书处。送暑曾过深港桥,寻秋每唤瓜洲渡。”说这里本是适合诗人居住的地方,更何况还是古贤读书的好地方。往昔的夏日,阮元曾经来过这里(深港桥)避暑,瓜洲渡也给阮元留下深刻的美好印象;
“送暑寻秋向枊村,藤床竹枕宿南轩。千章夏木全遮屋,八月秋潮直到门。”枊村指的是诗人王豫。阮元愉快地回忆起和诗人王豫一起在阮亨家做客的情景,卧于“藤床竹枕”享受“八月秋潮”是何等的惬意与浪漫;
“门前月色连清夜,稻花香重荷花谢。记得曾叹北固秋,何缘又结西湖夏。”阮元还记得和诗人王豫一起游北固山的难忘时光,今天又在杭州西湖相逢盛夏,岁月如梭,就如同“稻花香重荷花谢”那样匆忙;
“今日披图似梦醒,涛声还向梦中听。钱塘八月西楼卧,错认扬州江上亭。”今日题《曲江亭图》时仿佛如梦初醒,昔日长江奔流的广陵涛声只能在梦中倾听了。现在钱塘的府邸里,竟然把巡抚衙门错当着扬州的曲江亭了。阮元虽然身居高位,但是见到家乡的《曲江亭图》时,仍然免不了产生殷殷的乡愁,可见思念家乡扬州的情结是多么的浓郁。
阮元在瓜洲还留有其它文墨。比如,阮元在漕督二年以来,回空重运一万六千余船,无一船漂失亏米者,前督无一人做到,嘉庆帝大悦。阮元如此顺利,功高业彰,深信有“江、风”二神护佑。因此,四月,阮元在瓜洲修缮“江、风”二神庙,并奏请嘉庆帝书赐“江、风”二神庙匾,奉谕:请阮元代书“恬波利涉”悬挂殿额。
总之,先贤阮元,在外为官宦迹之地都留下了政绩文韵等佳话,在家乡的瓜洲也传颂着他的诗词歌咏、义造红船、创设“焦山书藏”、代书“恬波利涉”匾额的故事,他的诗情,义举,雅事诠释着一代通儒的仁者之心,官者之德和诗者之志。
